那些憂傷的年輕人
- Published on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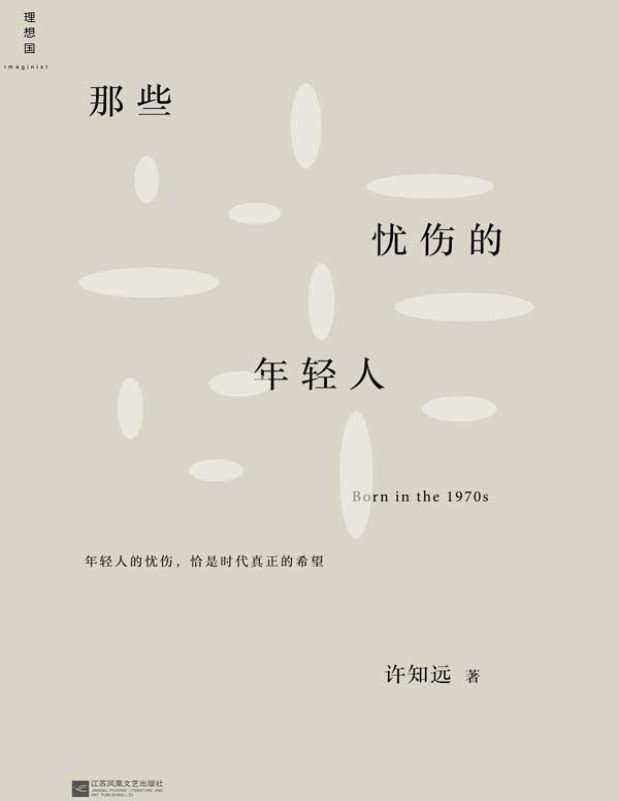
忘了最一開始是誰安利我的,但十三邀這節目看得很早,這是一個少數我會常去刷看有沒有更新的節目,可以說是我的精神糧食之一。當輿論討厭這節目時,就說許知遠的打扮不尊重與談者與觀眾,說他自戀自負,從社會經驗上看去有點笨拙,剪輯冗長不流暢很尷尬;當輿論喜歡這節目時,就說許知遠真實做自己,說他擁有這時代稀缺的理想,笨拙中透露著可愛,剪輯手法還原真實保留的原汁原味。如果你還記得村上春樹《挪威的森林》這例子,想必不會有任何的困惑。
因為這個節目,我認識了很多人,很多很厲害的人,當然是單方面的。知道了金承志,也愛上彩虹合唱團,讓我清楚有趣是難能可貴的特質,是有必要細心呵護的。知道了馬東,印證了我的猜測:那些看似嬉笑怒罵的人,能在公共視野被看到,也肯定是有很高的格局,藏的很深的思想,沒什麼是只憑運氣。知道了唐諾,想到這樣的讀書人,平常就如此普通的在我熟悉的台北生活著,我突然對這城市充滿敬意。還開了很多眼界,總之我謝謝這個節目,媒體還是可以有更積極的意義的。
其實我今天想談的是《那些憂傷的年輕人》這本書。這本應該是許知遠在北大接近畢業或剛畢業那一段時間寫成的書。他在 20 年後重寫的序言說了,有時候生命就是如此神奇,這些青春時代留下的文字似乎預言了他之後會走的路,且也謙虛的說,現在走的路也沒超過當時的框架。我想說,這是多麼大的成就,在某種意義上,他成為小時候想成為的人。
書中很多主題我看起來非常有共鳴,就覺得能明白他寫下這些文字時狀態的各種細節。可能也在相似的年紀,可能也對文學有天然的喜好。我摘錄一篇吧:
〈文學青年〉
這好像是 1980 年代的故事,那時候最流行的求愛方式是,路上攔住一個姑娘說:“你喜歡文學嗎?”你要裝得一臉惆悵,似乎充滿了對祖國前途的憂慮,還有對整個人類精神世界的關懷。然後你特別深沉地和她談文學,談那些文學大師的追求。這時候,姑娘肯定會被你滔滔不絕的天才迷惑,滿眼都是虔誠的欽佩,然後特別心甘情願地跟你走。那時候文學青年是個搶手的稱號,對於異性具有特別的誘惑力。這些東西現在看起來像傳說或者一出滑稽劇。
自王朔出道以來,文學什麼時候開始淪為貶義詞了,好像張口談文學的人都是些大尾巴狼。我記得一天晚上散步遇見一對,他們好像剛剛認識,男子還處於求愛階段,於是我就听到了一句特別具有戲劇效果的話:“我喜歡文學。”這句話在鬧哄哄的大街上如此動人心弦,我差點兒就被感動了。這時候,他們身邊路過一個騎車的哥們,他在那個嬌羞的女子尚未反應之前,大聲說:“我也喜歡文學。”然後匆忙地騎車過去,留下一片放肆的笑聲。這時候那種純情的場面一下子就被糟蹋了,一下子就打破了文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……
我有時候也犯這種傻,我跟一個新認識的姑娘在談米蘭·昆德拉的時候,她就向她周圍的人介紹我是一個文學青年。你可以想像那些傢伙的表情嗎? “文學青年,文學青年”,他們不斷搖頭,就像阿 Q 說的“女人,媽媽的,女人”。而且我發現大家都特別喜歡用這個詞來嘲笑人,要是罵一個人傻,比如看到我,他們準會說:“喲,文學青年又來了。”
我從此就接受了這個教訓,再見姑娘的時候就大談時尚問題,閉口不說任何和文學有關的話題,即使提到也是裝出一臉特不屑的樣子,然後把那些東西嘲諷一番。這種方法真的很有效,因為姑娘們都露出了親切的目光。但是當我一個人的時候,還是喜歡讀一讀文學,還是喜歡讓自己被那些大師們熏陶一下,而且我猛地發現那些滿臉特別不在乎文學的人也和我一樣,而且讀書讀得越多的人越裝得庸俗,越喜歡嘲笑文學青年。我差不多明白他們的意思了,文學是自己體會的,不用老是拿出來炫耀,而且越是那些半瓶子醋越喜歡拿出來晃蕩。所以,我也開始喜歡拿文學青年罵人了。
看到這,我心中想,沃草,不只是我們這一代,原來對文藝青年的歧視是淵遠流傳的。沒錯,書讀得多的人越喜歡裝的庸俗,而我就是書讀得少,怕你不知道,才在這邊跟你談書的。
不過,我還是憧憬著,那天我們社會能進步到談論文學藝術是一件很酷的事的狀態,一個精神能量也被納入考量的先進社會。就像平時朋友間的對話多嬉笑怒罵,但我心底還是渴望著有深層細膩的交流,可能因為有過這樣的經驗:太多再見是很難再見的,那一轉身後不知道何年何月再相逢,或即使再見到了,事隔多年,也物是人非。這或許是我討厭桌遊及愛喝酒的原因。我不想玩著沒意義的遊戲,不想尋著廉價的開心。想與你談小時候、談最大最不真實的夢想、談所有經歷過的荒唐事。我也知道喝酒後臉紅著一塊一塊的不好看,喝多了會頭痛,但就想先主動卸下自己的偽裝,希望能有一次真實而純粹的交流。我想起那些很久之前真心的碰撞,在記憶的長河裡熠熠生輝的向我揮手,這應該就是我最寶貴的資產了。還是那句老話:只有真心相待,不以禍笑柔色應酬,人生才有華彩。慘了,我又失態了。
就讓這文章在這邊結束吧,雖然原先是想聊許知遠的,但我猜這樣的發展,本身就很許知遠。
後記:關於文青,還有幾點想補充:
- 後來思考,裝或勉強是無可厚非的,裝著裝著不想破功就得加強自己,假作真時真亦假,無為有處有還無。且文藝是有高門檻的,是需要經過學習的,總有過渡階段。
- 上上一代人,書看得多,文青較多,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生活中沒有其他娛樂,搞個 Xbox 回到過去,估計就沒人要看書了。正如歐洲地鐵上,很多人看書的原因只是他們網路真的太爛了,坐上 Ubahn 基本沒網路。
- 文青內部的鄙視鏈才是令人鄙視的。
- 不知道為何,整個許知遠的狀態,讓我想到王文明。